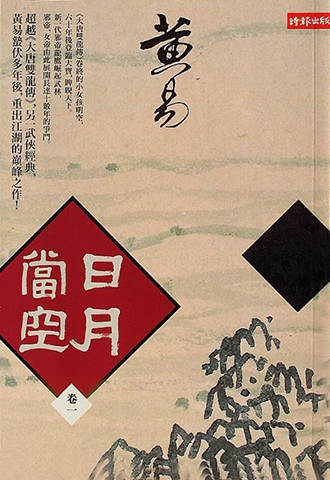沙成山冷冷地道:“无忧婆婆还好吧?”
一个女子尖声冷叱道:“少套交情,我们兵分四路找你,可不是找你套交情来的。”
沙成山摸着自己的脖子,道:“这个我知道,无非是沙某项上人头而已。”
那女子平举着蛇尾尖刀,低吼道:“你知道就好,沙成山,如今你已经身受重伤,识相些先让我们把你捆上,送上湘江无忧门,是生是死,你去对我们门主说去,如果你想挣扎,便只有割下你的人头了。”
沙成山淡淡地道:“如此对我,已是相当宽大,然而我却有要事在身,实难令各位满意,真是抱歉了。”
两个壮汉,不错,正是“无忧门”八大护法中的齐大元与白虹二人!
这二人当然知道沙成山的厉害,但那是在乎时,如今沙成山身受重伤,他们就宽心地找上来了!
此刻,白虹重重地道:“沙成山,沙河岸你杀了七个大汉,后来才知道那是七个横行大漠的‘沙漠七虎’,当然,令我们高兴的是,沙成山,你果然受了重伤。”
冷冷的,沙成山道:“尊驾以为有机可乘?”
齐大元笑笑,道:“绝非乘人之危,事不得已,沙成山,你只能怨造化弄人。”
沙成山道:“我从不怨谁,不过有时候会对我自己有所抱怨,因为,这一阵子我好像有些婆婆妈妈。”
一个紫衣女子尖声道:“什么叫婆婆妈妈?”
沙成山一笑,道:“我抱怨这一阵子我出刀总含着一份悲天悯人的心肠,好像有人这么说过——对敌人慈悲便是对自己残忍。”
他重重地看着对面四人,又道:“这句话我此刻才深深的体会到了。”
不用解释,更不用多言,沙成山的话令对面的两男两女心中明白。
是的,方家集“无忧婆婆”率领他们搜找宝物的时候,沙成山有能力搏杀他们,然而他没有,就这件事而言,便与他沙成山一贯的作风相违背。
而现在这四个刀下游魂反而找上门来了。
就在这时候,“无忧门”的两男两女便毫不迟疑地跃下马背,白虹抖着手中蛇尾尖刀,厉声叱道:“沙成山,今天你就认了吧!”
齐大元也重重地道:“沙成山,最后一次机会,你如果愿意跟我们回转湘江‘无忧门’,至少还可以活到湘江,否则必叫你立时血溅当场!”
沙成山轻轻摇摇头,翻身下马,他恹恹地道:“很抱歉,怕要令各位失望了!”
四个人的动作真正是其快如飙。
两个壮汉并肩弹腿,蛇尾尖刀宛如两股冷电流闪,未及眨眼工夫便罩上敌人头顶。
比白、齐二人更快的是两个女子,那种贴地卷至的身法,立刻令沙成山忆及去年在山顶上援救方捕头时候,两个“无忧门”女子的身法。
未见双肩晃闪,宛似风刮柳梢般,沙成山僵硬地横移丈五,
就在四人一错而过的时候,沙成山又复归原地。
沙成山刀未出,他冷沉地道:“等等!”
一个女子声音道:“沙成山,你想通了?”
白虹已微愠地道:“束手就缚总比血溅当场好得多,沙成山,人在某一个运蹇的时候,最好光棍点,也免得吃眼前亏!”
沙成山淡淡地道:“四位千万别误会,沙某只是想弄明白一件事情。”
一个紫衣女踏前一步,叱道:“真不干脆,你还有何话说?”
沙成山道:“我很想知道,贵掌门无忧婆婆为什么一定要割下沙某的项上人头?”
两个紫衣女对望一眼,齐大元已重重地道:“两个原因,但我们只明白其中一个原因。”
沙成山道:“请讲!”齐大元道:“沙成山,难道你忘了,你曾为了援救方宽厚而击杀我们门主身前的两位侍女,你以为就这么简单的完事了?”
沙成山淡淡地道:“只怕这只是你们的藉口,真正的原因,怕不会是如此单纯了。”
四人对望着,白虹冷沉地道:“不错,沙成山,实际上的确不单纯,除了取你项上人头之外。”
沙成山道:“如此说来,贵门主要取我项上人头,并非是为了替她的两名侍女报仇了?”
一个紫衣女叱道:“你话问完了没有?”
沙成山一声哼,有些像是自言自语地道:“看来我这项上五金魁首越来越值银子了!”
白虹吼道:“沙成山,你在说什么?”
沙成山道:“加上你们‘无忧门’,如今要争夺我项上人头之人还有方宽厚与‘苗疆百毒门’,这件事怕真的不简单了。”
白虹大吼一声,道:“沙成山,就叫我们‘无忧门’捷足先登吧!”
他“吧”字出口,声似刺耳怪吼,蛇尾尖刀再次往沙成山杀过去。
另一面,两个紫衣女也齐声尖叱,道:“杀!”
四把蛇尾尖刀来自四个方向,却又刺向四个部位,尖刀如电,冷芒激闪,“咻咻”刀声窒人鼻息。
沙成山再次横移半丈,“弯月刀”脱袖而出,一片光华猛然翻闪如电,空气立时激涌呼啸,围上的四人立时连连倒翻,鲜血已然迸溅。
“好畜牲,你尚能垂死挣扎几时?”翻出三丈外又腾身而起的白虹,口中大骂。
伸手摸着耳根鲜血,齐大元问附近惊悸的两个紫衣女,道:“二位的伤如何?”
一个紫衣女抚摸着右肩头,道:“尚可再杀!”
齐大元立刻高声,道:“记住,不可盲进,觑准了下手,往要害地方下刀,娘的,姓沙的可是身受重伤之人。”
沙成山冷冷地道:“四位,别逼我,你们应该心里明白,我为什么不对你们下狠手的原因。”
白虹怒叱道:“你无力下狠手,沙成山,因为你已身受重伤。”
沙成山摇摇头,道:“四位,你们各门派皆要我项上人头,这中间一定有人暗中主使,在我未弄清楚此人是谁之前,我不想再多伤人。四位,沙某说得够清楚了吧?”
齐大元冷冷地道:“你唬谁?”
一个较高的紫衣女手捂着臂上刀伤,道:“二位护法,我们还等什么?”
白虹咬咬牙,道:“对,我们还等什么?”
沙成山狂吼一声,道:“你们真是猪,果真要死绝吗?”
四个人怎会听他的吼?
两个紫衣女高声尖叱,道:“沙成山,你死吧!”
两把蛇尾尖刀交叉闪耀着冷芒,快得宛似追逝过去的时光般往敌人刺去,齐大元与白虹更是发疯般地从两个方面兜截。
雷吼一声,沙成山道:“好,来吧!”
他不移不动,出手却快疾准确,伸缩之间,刀芒弹掠舒卷,极光扩展,宛如可遮天盖地。
于是,金铁的交击声盈耳不绝,任是四人动作如电,却是尖刀皆被阻于敌人身前三尺地,再想进入半寸也休想。
白虹身受三处刀伤,有一处可见森森白骨,他那粗壮的身子打横里一阵晃荡而没有倒下去。
白虹咬牙不吭声,却在他站定身子的时候,抽冷子猝然又扑进,他的左手便又多了一把匕首,人已到了沙成山身后,他才沉声道:“老子陪你一齐上路吧,我的儿!”
蛇尾尖刀上了半天空,匕首却猛然挑上沙成山的背上,真是白虹神来一刀。
白虹的刀刃沾肤——实际上刀刃划上了他的伤口上面,沙成山凭着搏杀的经验,立刻往前冲出三丈远。
然他的前扑之势中,“弯月刀”左右向后暴闪九次。
怪叫着,白虹结实的身体渐渐往地上矮去。
他看着沙成山从他的匕首下走去,眼珠子都憋出来似的,张口说不出话来,直到他双膝跪在地上。
双肩头面,一团模糊,白虹至少挨了九刀。
齐大元刚刚站定身子,回头发觉这一幕,便不由得厉吼一声,道:“白护法!”
两个紫衣女子落地挣扎着站起身来,却已无力再杀,怒视着沙成山。
单膝跪地扶住白虹,齐大元道:“振作点,白护法,你要振作点!”
白虹望着左手匕首,匕首上面在滴血……
他苦笑一声,道:“你们看,这是沙成山身上的血,他也挨了我一记狠的!”
齐大元点点头,道:“够了,姓沙的也淌了血!”
白虹道:“真恨,这一刀为什么没有招呼在沙成山的要害处?我原是要送进他后心内的……”
忙着取出一把丸药,塞入白虹口中,齐大元道:“快服下去,别再说了!”
那面,沙成山已缓缓走近马身边。
是的,他那背上一刀是戈二成他们替他挂上的,如今也真是巧,仍是那个地方,又再补了一刀,是幸运?还是倒霉?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天知道。
沙成山爬上马背,他冷冷地望着四人,淡淡地道:“回去吧,且问清楚贵门主,为何要沙某项上人头,如果她有充分理由,沙某自会把人头送上门,否则……”
齐大元沉声道:“沙成山,你逃不掉的!”
沙成山摇摇头,道:“我不会逃走,沙成山永远面对现实!”
于是……
一场搏杀就此结束——暂时的结束。
是的,“无忧门”不放过沙成山。
“苗疆百毒门”也等着取他的人头。
甚至连退职的方捕头也在“狗”视眈眈地找机会要取沙成山的性命!
为什么会演变成这种局面?沙成山真感迷惘了。
现在,沙成山缓缓地到了方家集,五更天天刚亮,方家集的街上没有人迹。
有,平安客栈的伙计正伸着懒腰打着呵欠走到栈房门口来。
马蹄声令他抬头看,不由得笑起来:“哟,是胆子大的客官又来了,你的篷车……”
沙成山爬下马,伙计才一惊,道:“我的乖,你背上挨刀了!”
沙成山把马缰绳交在伙计手上,道:“而且还不轻!”
伙计指着沙成山泛青的手背,又道:“还有你这手背上,伤的也不轻。”
沙成山一声苦笑,道:“而且还有毒!”
伙计笑笑,道:“没关系,我马上把老大夫替你请过来,这些伤他一瞧就好!”
沙成山道:“先给我弄个房间……”
伙计指着客栈房内,道:“还是你原来住过的那一间,去吧,我先请大夫去。”
一锭银子塞在伙计手上,沙成山道:“把银子带在身上,那位老大夫认银子不认人。”
伙计笑笑,低声不好意思地道:“方家集就是那么一位大夫,他虽然要银子,可也救了不少人,客官,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方家集只有他一个?”
沙成山摇摇头往台阶上走,道:“我怎么会知道?”
伙计道:“他的医术高明,原来三家药铺,自从他一到方家集,哈哈,另外两家半年不到全迁地为良了。”
沙成山走进客房中,自己刚刚坐下,另一个伙计已走进来。
伙计手提着茶壶,笑道:“客官,这几天你去什么地方了?篷车还在后院里。”
沙成山叹口气,道:“暂时我还用不着车子,先替我送些吃的来。”
提起篷车,沙成山心中一阵痛,那辆篷车原打算给兰妹母子二人乘坐,岂知变生肘腋之间,那么不幸地便使她母子失去踪迹。
沙成山怔怔地坐在床沿上,他实在想不透兰妹到底落在何人之手。
就在这时候,平安客栈的丁掌柜抚着山羊胡子走进来,道:
“客官,你总算回来了。”
沙成山奔驰一夜,叹口气道:“掌柜的有事?”
丁掌柜笑道:“是这么的,上次你放了银子在柜上,大部分是为你的那位鹰眼似的朋友疗补身子,经过前后一并折算,银子方面……”
沙成山道:“不够?”
“够了,够了!”丁掌柜又道:“尚余十七两八钱,不知客官你……”
沙成山道:“暂时搁着,以后再说吧!”
便在沙成山刚刚吃过早饭,门外面匆匆进来三个人。
伙计指着两个老人,道:“我请张大爷前来,正巧遇上他的老友也在,二人就一同来了。”
沙成山看了张大夫一眼,道:“请问这位老人家是谁?他怎的也来了?”
这位老人团脸灰发,鼻子奇大,只是脸皮有些僵硬得宛如贴了一张纸。
张大夫笑看着团脸老人,道:“别问他是谁,先由我看看你的伤再说。”
沙成山先把左手平举着,道:“半条臂有些麻麻的……”
不料张大夫一看惊异地道:“这是被毒物咬中的,好家伙,这种毒奇浓,中的人非死无异,你能挺着找上我,也算是你的命大。”
沙成山又把上衣脱掉,张大夫伸手在伤口四周按着,边问道:“这地方痛不痛?这地方又是怎么痛法?是刺痛?木痛?闷痛?抽痛?”
沙成山说出自己的感受来。
张大夫点点头,道:“乖乖,真是命大!”说着回头对团面老者笑道:“未伤及经脉,真是幸运,扁兄你看……”
沙成山猛孤丁回头直视团面老者。
老者已伸手在自己面皮上一阵揉搓,只见假皮纷纷落下来……”
团面老者以袖拭面,笑道:“沙成山,我们死里逃生地又见面了,哈……”
沙成山怔怔地道:“原来真是扁老呀,你……”
不错,团面老者正是易容大师“千面老人”扁奇!
沙成山激动地拉住扁奇一手,道:“扁老,是沙成山把你老的幽清之地搅翻,害你如今四处飘荡……我……”
扁奇抚髯哈哈笑起来,道:“人都是怪物,静极思动,动极思静,我老头儿是静极思动,这几个月我可走了不少地方,也看过不少鲜事,当然也就长了不少见识,倒是你老弟,还真令我老头儿放心不下。说真的,你那怀有身子的老婆呢?那真是位好姑娘,你可要好好对待她哟。”
年纪大的人是唠叨了些,也是常情,但扁奇的话令沙成山顿感心热。
是的,这些天几乎已分不清谁是好人谁又是坏人,真难得听到老人家如此的关怀,遂苦兮兮地道:“扁老,别提了,我的兰妹生了个儿子,五天不到便母子失踪了,唉,我沙成山这些天正为此事南北奔波不已……”
扁奇也是一惊。
张大夫道:“像你干的这种行业,当初就不该有老婆,没得倒害了一对母子。”
扁奇怒视着张大夫,叱道:“张爱宝,你如果指责我这位沙老弟,小心我老头儿同你绝交。”
张爱宝忙低声地道:“不说,不说,好了吧?我为他疗伤祛毒吧。”
张爱宝一边忙着替沙成山疗伤,一边自言自语道:“普天之下我只有向你扁老大与药老三低头,娘的皮,就好像你二人是我的克星!我……认了。”
沙成山心中在想——张大夫口中的药老三,难道就是苗疆名医圣手药老子?
半个时辰后,沙成山睡着了,扁奇掩起房门,怔怔地坐在床边,张爱宝几次催他,他都不走,于是,张大夫回药店去了。
沙成山睡得真是香又甜,这一觉直睡到二更天。
扁奇见沙成山猛孤丁挺身子,真地吓了一跳,道:“老弟台,你醒了?”
沙成山下得床,道:“扁老,什么时辰了?”
扁奇道:“离子时尚有一个多时辰。”
沙成山道:“糟了!”
扁奇道:“什么事情糟了?”
于是,沙成山对扁奇道:“我把秦百年女儿秦红囚在山洞中,言明三天到四天,一定放她出来,子时一到我岂不是失约了?”
扁奇道:“如果不远,你还来得及!”
沙成山道:“龙腾山庄要我两天内放出秦红,扁老,我原是今日早上便放人的。”
扁奇道:“不急,不急,你正可以把秦红掌握在手中,逼他们替你找出丘兰儿母子。”
沙成山猛摇摇头,道:“丘兰儿母子不是落在龙腾山庄或虎跃山庄,我沙成山就不能挟持秦红为人质,否则岂不落个奸险恶诈的臭名?”
扁奇摇头一叹,道:“君子争义,小人争权,沙老弟,你是我老头儿心目中的好样人物。”
沙成山忙叫进伙计,包了一大包食物,便立刻往方家集西北的槐树坡走去。
此刻,又是一个圆月当头的明月夜。
沙成山匆匆地跃过那个突出的危崖,闪身走入洞中。
沙成山并未开口叫,他小心地往洞内走着,便在这时候,微微的,他听到了哭声传来,心中不由吃一惊。
越走,哭声越清晰,正是秦红的声音。
沙成山遥遥地望过去,只见油灯影下,只有秦红一个人在那里,他立刻叫道:“秦姑娘,沙成山来了!”
里面,秦红拭泪望过来,道:“你说话不算数,为什么迟来一天?”
十分歉然地走近前,沙成山双手把一包吃的送过去。
秦红一掌打落地上,她双泪迸流……
沙成山一怔!
秦红已“哇”的一声扑进沙成山的怀里,她认真地嚎啕大哭起来了……
半晌,沙成山方才托起秦红下巴,道:“可愿意听听我来迟一天的理由吗?”
缓缓地坐下来,秦红这才拾起地上吃的,边吃边道:“好嘛,你说说你为什么晚回来一天。”
沙成山在秦红身边,他叹口气,道:“果然如你之言,丘兰儿母子并未在凤凰岭的龙腾山庄上。”
秦红道:“天下也不只是丘兰儿一个女人,真要是找不到她母子,难道你还要……”
沙成山重重地道:“我一定会找到她母子的!”于是,沙成山把这次凤凰岭的遭遇,详细地说了一遍!
当沙成山说到一路回来遭人截杀的事,秦红冷冷地不再开口了。
沙成山沉声道:“秦姑娘,你以为是谁在要我的项上人头?”
秦红白了他一眼,道:“干你这一行的,太多的人在等着割你的人头,我怎么会知道?”
沙成山突然道:“会不会是你爹?”
秦红全身一震,道:“我不敢说不可能,沙成山,你应该明白,这种事情我怎会知道?”
沙成山站起身来,道:“好了,秦姑娘,沙成山尚有事待办,你可以走了!”
秦红瞪着一双大眼睛,道:“你赶我走?”
沙成山道:“我同你爹,你舅舅,已是水火不相容,冰炭难同炉的地步,我们还是早早分手的妙。”
秦红道:“就这么轻松地分开?”
沙成山道:“那要如何分开?”
秦红道:“你违约晚回来一天,应该受罚!”
沙成山道:“怎样罚法?”
秦红想了一下,道:“我不能白白等一天,这样吧,你陪我在洞中坐到天明,天明之后各走各的,如何?”
沙成山睡了一天,精神极佳,又敷了张爱宝的灵药,连伤处也已结了痂,他此刻一心想到小村子上找那一对老夫妻,这时闻得秦红的要求,叹口气,便坐下来。
秦红挽住沙成山一臂,道:“我们谈一夜,也算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了。”
沙成山道:“最好是在高山之岭,大河中央,荒山野林无人地方静下心来畅谈,此刻我心乱如麻,哪有心情畅谈?怕辜负你了。”
秦红把嫩脸贴上沙成山肩头,道:“不谈也没关系,就这么靠在一起也是好的。”
沙成山道:“秦姑娘,我希望你立刻快马赶回龙腾山庄你舅舅家中,也免得你舅舅骂大街。”
秦红道:“已经晚一天了,再多半天有什么关系?”她突然伸手去摸沙成山的胡子,又道:“你也怪可怜的,一定在想丘兰儿母子了?”
沙成山点点头,道:“无时无刻不在想念,如果……”
秦红几乎把脸贴上去,她轻柔地问:“如果什么?”
沙成山道:“如果谁能指引我一条明路,沙成山必终其生地感激此人!”
秦红幽怨地道:“我虽贵为虎跃山庄大小姐,又有舅舅的呵护,但仍然没有丘兰儿幸运,唉!”
沙成山道:“丘兰儿的命太苦了,跟着我就生活在惊涛骇浪的日子里,大小姐,这种日子你是不会理解,也不会明白的。”
秦红双手搂住沙成山的腰,道:“沙成山,你难道不为我的付出而动心?”
沙成山枯井不波地道:“我是个大男人,怎会不知道秦姑娘的心意?然而我不能,人要有自知之明,秦百年是容不得我的!”
秦红道:“你没有表示,怎知我爹不答应,如果你能忘却过去,我就同你一起回狮头山去。”
沙成山道:“可惜的是我无法忘却过去,更不会忘记丘兰儿母子!”他一顿又道:“秦姑娘,怕要令你大失所望了。”
秦红突然笑笑,道:“没关系,沙成山,我会等,等到丘兰儿真的失踪,甚至……”
沙成山吼叫道:“不要说了!”
秦红并不生气,她淡淡道:“不说便不说,何必生那么大的气。”
沙成山深深地叹口气,道:“对不起,秦姑娘,我有些失态。”
秦红嘴角一牵,道:“没关系,如果想同大镖客沙成山厮守在一起,就必须承受你这般的吼骂,嘻……”
沙成山抬头,四目相对。
秦红的脸孔绯红中带着一份渴求。
是的,那是女子特有的表征,沙成山在柳仙儿身上没有发现过这副样子。
因为,柳仙儿看得淡,看得平淡的人,脸上是不会有这种醉人的艳红。
秦红就不一样了,狮头山下的虎跃山庄大小姐,看来对于男女间的事还陌生得可怜。
谁也没有说话,然而语音在二人的心中激荡。
秦红心中在小鹿也似地撞击着:“沙成山,你这小子,怎么会不敢动手?你怕我会吃了你?”
沙成山心中有着矛盾,他实在难以理解,自己哪一点出色,竟然也弄得秦大小姐另眼青睐?
咬咬牙,沙成山猛地搂住秦红的腰。
只是嘤咛一声,秦红已倒入沙成山的怀里不动了。
似乎是——山雨欲来风满“洞”的光景吧。
沙成山有着同秦红卯上的冲动,他那满嘴粗胡子便一个劲儿地在对方的嫩脸上、脖子上,甚至胸前磨蹭着。
秦红口中发出“咦唔”之声不绝,两只手搂得更紧了。
于是,就在一阵拥抱与热吻中,沙成山的手触及到秦红的衣扣。
他摸了一阵子未解开,秦红却自动伸过手来,不料沙成山猛孤丁一把按住秦红的手,他仰起头来。
秦红一愣,立时把半闭的美眸睁大,她愣愣地看着几近痴呆的沙成山。
沙成山浓重地叹了一口气,道:“对不起,秦姑娘,我失态。”
秦红有些哽咽地道:“是我,是我……愿意……”
沙成山道:“但我却不能……不能因为自己心中对你爹这怀恨,而毁了你的清白。”
秦红重重地道:“宁愿把清白交给你,也不愿给那个庸俗的哈玉。”
沙成山道:“算了,就让我们做个纯洁的朋友吧。”
秦红似是懊恼地道:“沙成山,你大概不是为了我的清白吧?”
沙成山道:“我实在不愿轻易坏了你的名节。”
秦红猛孤丁跳起来,道:“什么名节?什么清白?你的心中去不掉为你生子的丘兰儿,你想到了丘兰儿,你仍然忘不了她。沙成山,你心中对她产生愧疚,便不敢接受我对你的爱意,是吧?”
沙成山点点头,道:“我不否认!”
“你还是承认了?是吗?”
“当然,大部分也是为了你的名节,秦姑娘,沙成山不是浪荡子,更非江湖上淫徒之流,如果我接纳了你,此生我便要对你负责到底。”
秦红咬着嘴唇,道:“如果你是浪荡子或淫徒,我早就不屑于找来了。”
沙成山叹口气,道:“原谅我,秦姑娘,在未确定丘兰儿母子二人的生死存亡前,我不能接受任何人的爱意,秦姑娘……”
秦红猛地又抱住沙成山,道:“沙成山,你虽然拒绝我的爱,但我并未看错人,你是一位真正的侠士。”
秦红伸出双手托住沙成山的毛脸,蜻蜓点水似地在沙成山的唇上吻了一下,回头便走。
沙成山忙追上前去,道:“你现在要走?”
秦红未回头,轻声道:“你愿意送我一程吗?”
沙成山道:“应该的!”
秦红道:“你不是要上那个小村子吗?”
沙成山道:“是的,但我还是要先送你,因为我曾经答应江厚生,两天之内送你回龙腾山庄。”
“不是已经晚了吗?”
“是的,晚了一天,但你只要回到凤凰岭上,我还不算对姓江的失约。”
缓缓地走出山洞,沙成山与秦红二人双双赶到平安客栈外,沙成山叫开店门,开门的伙计愣住了。
沙成山道:“快把我的马牵出来。”
伙计匆匆拉出乌骓马,对沙成山道:“客爷,你的篷车是不是……”
沙成山道:“暂时不用,好生照顾着。”
秦红跃上马,低头道:“沙成山,你不是要送我吗?”
沙成山点点头,道:“秦姑娘,我送你过沙河。”
秦红道:“一马双跨?”
沙成山立刻对伙计道:“再拦匹马来!”
秦红突然跃下马,道:“不用骑马,我们走路。”
沙成山接过马缰绳,道:“也好,我拉马送你。”
伙计见二人往街头走去,愣然站在栈房门口,自言自语地道:“那个女子会是谁?”
秦红果然未再骑马,两个人并肩走着,谁也未再开口说一句话,秦红没有,沙成山也没有。
然而,沙成山十分清楚,秦红一定知道她爹的阴谋,甚至江厚生的阴谋,凤凰岭上张长江就曾经说过——“大计划”,难道秦红会不知道?
秦红当然知道,但秦红也明白,她想把沙成山这种一流高手拉到爹的身边,此时怕尚无可能,自己的行动是瞒着老爹的。
原来秦红找上沙成山,不只是她心慕沙成山的为人,更重要的是沙成山的武功,他相信,爹爹如要完成武林霸业,沙成山就是不可或缺的人才,因为一个沙成山,要比辽北黑龙堡的力量可靠得多。
二人各怀心事,然而,秦红却怀着可怕的心事,沙成山自然不会知道。
春阳露头,前面一道山岗,沙成山指着前方,道:“十里岗,秦姑娘,我们已离开方家集十里了。”
秦红笑笑,道:“轻松走路也蛮愉快的!”她俏目望向沙成山,又道:“你知道我为什么不骑马?”
沙成山淡淡地道:“不知道!”
秦红道:“你答应送我到沙河,沙河距离两百里,骑马不用一日,为了多相聚一时,所以我选择走路。”
“秦姑娘用心良苦,但我心中却一直悬念着丘兰儿母子,所以……”
“所以你一直苦在心里,沙成山,是吗?”
“是的,我心中是很苦,但为了感谢秦姑娘的青睐,沙成山苦也认了!”
秦红咬咬牙,道:“沙成山,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!”她顿了一下,又道:“当然,我也会以相等代价为你做一件事情。”
沙成山道:“请讲!”
秦红道:“答应我,不与我爹为敌!”
沙成山脸皮一紧,道:“我不够资格,秦姑娘,我凭什么去同你爹为敌?”
秦红道:“你的忿懑,也可以说是一腔热血。沙成山,你只要不同我爹为敌,什么事情都好办。”
沙成山冷冷地道:“包括你昨夜的表现?”
秦红脸色一寒,道:“沙成山,我不会令你吃亏的,只要你不与我爹为敌,秦红帮你找丘兰儿母子。如果……如果她们确已不在人间,我会挺身而出,不顾一切地嫁给你,为你生孩子,为你做羹汤,为你……”
沙成山全身猛一震,道:“秦姑娘,你能告诉我,有什么理由我会与你爹作对?”
秦红道:“以你的作风,因为你是‘二阎王’沙成山!”
咬牙未再开口,沙成山双目一紧,他低沉地环视四周,双目炯炯地绕行在十里坡官道上。
蹄声十分有韵律地发出“滴答”声,然而沙成山已似乎闻到一股子血腥味。
不错,他曾在这坡上同“西陲二十四铁骑”拼过命,这地方对他并不陌生。
此刻,坡上的那座破庙前面,一排站着四个人,沙成山没有多看,他拉着马低头走向场子的另一端——那是下坡的官道。
秦红却惊异地叫道:“关大哥,你们都来了?”
沙成山停下脚步,对秦红道:“有人接你了,秦姑娘,看来我不能送你到沙河了!”
那面,四个大汉并肩走过来。
不错,四个人之中有三个沙成山认识。